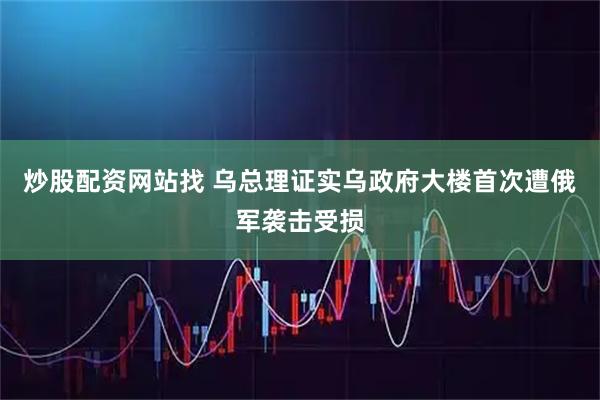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炒股配资网站找

如今,远程办公越来越普遍,数字游民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曾经以45岁以上人群为核心的旅居市场中,年轻群体的占比悄然上升至31%。介于旅游与长期居住之间的旅居正在打破“养老专属”的刻板印象;目的地选择从传统“山水秘境”转向配套完善的都市圈。
现在的旅居,可不只是简单地“找个地方住”,它包含了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当地社区的融入,还有对当地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等方面的综合需求。
年轻群体占比攀升 旅居打破“年龄壁垒”
长期以来,旅居被贴上“养老”标签,45岁以上人群尤其是60岁以上的退休群体,始终占据市场核心。但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格局正被打破。澎润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居住宿市场洞察报告》指出,年轻群体在旅居市场的占比已达31%,自由职业者、学生等群体的参与度显著提升,其中自由职业者的旅居比例远超其他职业类型,成为推动旅居“破龄化”的关键力量。
从行业分布看,金融、科技、自媒体等领域的从业者,成为年轻旅居群体的主力军。这类行业高度依赖数字化工具,远程办公适配性强,“旅居+工作”的模式与其工作节奏天然契合。00后的旅居者妙妙便是典型代表,她向记者介绍,从2024年毕业后,自己每隔个把月就会换一座旅居的城市。文案策划、跨境电商、商务执行……她利用实习期积攒的资源以及本地兼职群找到各种兼职,在安吉、大理、厦门、西双版纳等多座城市间过起了旅居生活:“至少现阶段,我希望带着好奇心行走在生活中。”相比之下,传统制造业、零售业等对固定办公地点要求高的行业,从业者旅居比例仍相对较低。
在旅居时长与频次上,1到3个月的中期旅居占比最高,不足1个月的短期与超过3个月的长期旅居各占约30%;多数旅居者一年出行不超过3次。这意味着,相较于短期度假,旅居能为旅游市场贡献更稳定、持续的住宿需求,也折射出人们对“沉浸式体验某地生活”的需求已超越“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
居住体验上,私密性成为旅居者对“安全感与舒适度”的核心诉求,居住模式的可选择性也备受关注。预算方面,多数旅居者月均住宿预算在6000元以内(日均200元以下),对应经济型与中端住宿产品;仅约10%的人群愿意承担月均1万元以上的费用。
都市圈成新宠 配套优势超越“慢节奏”
和旅居人群年龄结构变化同步的,还有旅居者核心需求的改变。调查发现,现在的旅居者考虑的因素很全面,更愿意选择城市综合配套好的旅居地,而非单一优势突出的区域。其中,环境质量和社交氛围并列成为最受关注的因素。
传统观念中,旅居目的地应是云贵、川渝等“慢节奏、原生态”的区域,但数据显示,长三角、京津冀及沿海地区已成为旅居者的首选。这种“反常识”的选择,本质是旅居者对“便利性”的极致追求。
对年轻群体与数字游民而言,旅居的核心是“入世”而非“避世”。《报告》中,一名35岁的咖啡品牌创业者通过“旅居试水”选址的经验是,沿海城市消费水平、商业氛围更适合咖啡品牌生存,他在青岛、江浙多个城市住过,既体验了当地生活,也摸清了市场,一举两得。
在环境需求上,旅居者更看重空气质量、水质、温度等基础宜居要素,自然风光的权重反而靠后。社交氛围的重要性,则凸显了旅居者对“归属感”的渴望。无论是数字游民还是康养人群,都试图通过旅居打破孤独感,文化资源、社交机会、远程办公支持成为关键诉求。一名22岁的受访者偏爱长三角地区,她认为这里的音乐剧、话剧巡演从不缺席,线下文化活动密度是其他地区比不了的;另外一名受访的艺术行业自由职业者则表示,近年来一直在多个城市间切换办公,最终发现还是上海周边最适合自己:“上海的艺术氛围最浓厚,同行朋友多,累了就去杭州住几个月,周末看展、交流都方便。”
未来,对于旅居产业来说,目的地城市本身是不是宜居、便利、功能丰富,成了能不能吸引旅居人群留下来的关键因素。这样的城市,不仅要解决“居住三难”(房价贵、通勤远、选择少)的问题,还要打造一个“让人乐意居住、能成就事业、充满活力、有所作为”的综合生态环境,成为生活、工作、体验“三者合一”的承载系统。
比如说,上海长宁的“硅巷”,盘活了10万平方米的国有闲置空间,引入了500多家科创企业,打造了“24小时青年城区”。愚园路和武夷路等历史风貌街区持续“上新”,将文化社交和产业办公的场景结合起来,成为年轻旅居者的青睐之地。
县域旅居升温 “数字游民”变“数字乡民”
与城市群相对应的是,乡村、县城的旅居者“逃离城市”的初心也在悄然转变。如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开始思考生活的本质,乡村、县城这些不是核心城市的地方,正成为新一代旅居者心灵的归宿。这些区域以更低的生活成本、更松弛的节奏、更浓厚的人情味,以及渐趋完善的配套,吸引着人们从“短暂逃离”转向“长期栖居”。
“奔县热”带来的可不只是空间上的流动,还让人们的身份和生活模式都发生了改变。早期的旅居者大多觉得自己是“逃离者”,但现在,他们慢慢变成了“共建者”。他们参与改造闲置的农宅,把旧房子变成民宿、艺术工坊;组织当地的文化活动,挖掘乡村的非遗文化和民俗;打造共享农场,推动生态农业发展。比如在安吉县龙溪乡,数字游民们入驻DNA公社后,不仅通过远程办公创造价值,还带动了当地文创、电商直播等新产业的发展,从“数字游民”变成了“数字乡民”。
此外,“奔县热”还让乡村的资产得到了有效利用:大量闲置的农宅被盘活,农民靠这个实现了资产变现,地方对就业和技能培训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形成了“旅居促进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
全年龄段覆盖 旅居体验“千人千面”
旅居市场的未来,将是一个覆盖“0岁到90岁”的多元生态系统。《报告》指出,随着生活理念的转变,每个年龄段、人生阶段的人都可能产生旅居需求:数字游民需要灵活的“办公+生活”空间,亲子家庭追求“自然共处”的体验场景,长者群体渴望“身心调养”的康养环境。这意味着,旅居产品将告别“养老专属”“年轻人专属”的单一标签,成为覆盖全民、贯穿全年龄段的全新生活方式。
在此趋势下,旅居产品开发逻辑也开始从“单点产品”升级为“场景化解决方案”。例如,成都锦瑭养老社区体验中心,针对老年客户打造“全龄化养老产品”,整合住宿、康复、文化活动等功能;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则是国内首个专为数字游民设计的园区,构建“自然办公+社群共创+可持续生活”的复合空间;大理的NCC共居共创社区面向数字游民与创意人群,打造集住宿、办公、社交于一体的“生活场”。这些案例表明,未来旅居产品将更加细分,通过“千人千面”的体验设计,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社群让旅居者的生活不再局限于景区打卡、独居休息,而是进入“共享生活+多元体验”的新方式。数字游民通过社群实现跨地域的远程协作、兴趣共创;养老康养者则在社区中获得规律生活、温暖陪伴与精神慰藉。社群使“旅行”真正延展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阶段性行为。
无论是青年探索自我、跳出“内卷”,还是老年群体面对退休后的身份重构,社群都在扮演一个“情绪支点”和“成长加速器”的角色。年轻旅居者借助社群保持生活节奏与自我约束,在孤独中结识同行者;而康养旅居者则通过群体活动、集体仪式感,缓解孤独感,找到“有归属感的旅途”。
此外,社群还带动了空间经济的重新组合,让地方重新充满活力。像安吉县余村、成都市温江天星村、黄山市黟县NCC黑多岛这些数字游民聚集的地方,通过打造高质量的社区体验,举办持续的内容活动,营造共创文化,实现了办公场景、生活服务、文旅消费一条龙的产业联动。这些地方不仅吸引了外来人口,还重新优化了乡村空间的利用效率和运营模式。
社群不只是能给人当下的陪伴,还是未来生活的试验田。“迷你退休”(Mini-Retirement)这个理念,正从数字游民群体,慢慢传播到更广泛的旅居人群中。这个理念提倡一种“工作—生活—旅行”交替循环的生活节奏。在海南过冬、在大理深居、在青岛写作……远程办公的普及、移动生活的常态化使得越来越多人选择在中年阶段就开启中长期旅居模式。
文/本报记者 陈斯炒股配资网站找
九龙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